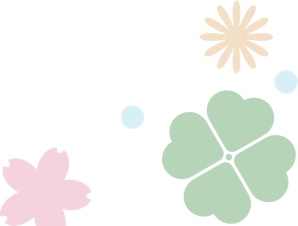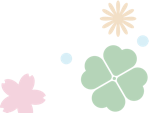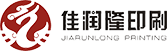hth:我家四代人代代有中国情缘
来源:hth 发布时间:2025-10-02 06:37:44
华体会 hth:
别说新加坡这个国度,就连我这个普通的家族,短短四代人,每一代人都跟中国有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和情感。
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,再过两天是新加坡、中国建交35周年,谨以此文,祝中国国泰民安,祝两国友谊历久弥新,两国交流合作深化巩固!
(中新建交35周年图片展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二楼举行,将持续至10月11日。欢迎光临。图源:新华社)
我祖上家贫,世居福建金门。现在,经常听到有“台湾金门”的说法,以讹传讹。我总是不厌其烦地更正——
金门孤悬海外,本来就是作为拱卫福建的海防要塞使用,土地贫瘠,并不宜居。到了明清,甚至
,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,就是从金门的料罗湾率水师出击。后来康熙收复台澎金厦,在金门也有过至少两次大战,哀鸿遍野。
1900年,光绪当了26年的皇帝。这一年,八国联军攻入北京。在遥远的黑龙江,则发生了江东六十四屯屠杀。
就在同一年,一个叫许嘉永的男婴,诞生在福建金门的后浦。金门的村落绝大多数是一村一姓,一姓一村。有句话叫“姓许徛后浦”,就是说后浦是许姓的聚居地。
在那个时候,金门还不是县,而是与厦门一样,归属福建同安县。清朝灭亡之后,1912年,政府把厦门、金门从同安独立出来,建立“思明县”。“思明”二字颇有来历,出自郑成功,就是“思念明朝”之意。这时的许嘉永才十一二岁,但就经历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二个政权。
金门土地贫瘠,而且缺水,风沙大,不适合耕作。与许多金门人一样,许嘉永自幼家贫,没有念过书,到了十多岁实在无法生活下去。与其在家饿死,不如冒险下南洋谋生。当时他20多岁。
幸亏熬过了海上险恶,许嘉永安全抵达新加坡。当时李光耀还没上小学,在家跟父母讲英语,跟外公、外婆讲峇峇马来语,跟其他小朋友则讲参杂着闽南语词汇的马来语。新加坡与槟城、马六甲一起,归属“海峡殖民地”,在英国人治下刚好满一个世纪。这是许嘉永经历的第三个政权。
虽然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,但是华人与中国关系极其密切。新加坡是清政府外派领事的首个城市;北洋水师曾两度正式访问新加坡。早在1906年,孙中山的同盟会就在新加坡设立南洋支部。自1911年,华人就占新加坡人口的四分之三,至今如是。
那个年代,南下谋生的绝大多数都是穷人、文盲。李光耀1978年就跟说过,“
我们新加坡华人是中国广东和福建等地南方人的后裔,祖先都是目不识丁、没有土地的农民;达官显宦、文人学士,则全留守中原开枝散叶,没什么事是新加坡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,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
跟大多数南下华人一样,许嘉永到了新加坡之后,只能当苦工,凭着金门人靠海吃海的本能,开了个手工作坊,以制造舢板为生,勉强还能维持生计。
不久后,1927年,妻子欧玉治也南下。欧玉治是金门欧厝人,欧阳姓、欧姓、区姓源于一姓,在金门聚居于欧厝。
。1931年,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,局势大乱。翌年,1932年,长子许乃火出世。这一年,欧玉治27岁。在那个年代,27岁才产子,算是晚育了。又过了四年,1936年,次子许乃顺出世。
许乃顺就是我父亲。我们家本来按“克、公、允、侯、嘉、乃、丕、绩”等字辈排列,不知为何,到了我这一辈,祖父决定不用“丕”而改用“振”。不过,到了我孩子这一代,我们又改回了“绩”。
。一直到1945年10月3日,金门才光复。很巧,10月3日后来是新加坡、中国建交的日子。
1939年,日寇封锁了中国沿海,中国只好开辟滇缅公路,从印度、东南亚经云南输入医药、弹药、武器等战略物资。在陈嘉庚领导下,
。我的母校——华侨中学就是陈嘉庚于1919年创办的,而我服务的社团——福建会馆和怡和轩则是陈嘉庚进行了改革,影响华社至今。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也对新加坡社会贡献巨大,他后来成为新加坡大学的首任名誉校长。新加坡大学是我母校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前身。
全面侵华之后,战局胶着,日本未能在“三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”,同时还面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制裁和石油、钢铁的禁运。为了给庞大的战争机器“输血”,
,日寇改名为“昭南岛”。这是祖父经历的第四个政权,当时他42岁,祖母37岁,父亲6岁,母亲王锦绣才1岁。还好他们在三年半惨绝人寰的日本占领时期都活了下来,才有了我。
不过,许多人没这么幸运。国既破,家亦亡。尤其为了报复华人支持中国抗战,
1945年8月15日,吃了两颗的大日本帝国无条件投降。英国人又回到新加坡了。这是祖父经历的第五个政权。
不过,当时在新加坡的华人除了少数取得英国国籍的,绝大多数仍是中国侨民,对故土中国的情感无法割舍,包括我祖母,一心向往回“唐山”探亲,也就是中国。一直到我念小学的70年代,
光复后的新加坡,百废待兴。民不聊生,教育简直是奢望。父亲念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,母亲连小学都没上过,终其一生,除了数字,唯一能写的字就是“王”。
父亲刚踏入少年时期,就发生大事。1949年10月1日,父亲13岁。这天,陈嘉庚踏上了城楼,参加了开国大典。翌年,他定居中国。七年后,陈嘉庚放弃英国国籍。
1961年8月12日,陈嘉庚在北京逝世,政府以国葬规格举行公祭仪式。在陈嘉庚之后的新加坡华社领袖,全都在新加坡落地生根。
1949年10月1日之后,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阻断了与中国的来往。许多华校生本来在高中之后可以到中国升学,但现在此路不通。1955年,在陈嘉庚之后继任福建会馆主席的陈六使带头
,成为全球范围内唯一在大中华地区以外的华文大学。南洋大学1980年停办,是新加坡国立大学、南洋理工大学的前身。
1959年,新加坡从英国取得全面自治权。那一年,副总理杜进才带头设计新加坡邦旗。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,
1963年9月16日,新马合并,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州。这是祖父经历的第六个政权。短短两年后,新马分家,新加坡独立,共和国政府成立。这是祖父经历的第七个政权。
。从他过世至今,快60年了,而新加坡共和国还是新加坡共和国,历经了那种风起云涌的历史时代的祖父,大概是想都不敢想的。
我孩童的年代,新加坡还有华校和英校。所谓华校,就是华文第一语文、英文第二语文,其他科目一律用华文教学,英校则相反。李光耀、柯玉芝夫妇是英校生,但他们的三个子女——李显龙、李玮玲、李显扬,则全是华校生。
,本是女校,后来虽然也招男生,但校名没有改,仍然叫“崇本女校”。母校早已停办,校址现在改为艺术中心。
。课外书都是看中文书,我小学就爱看历史故事、成语故事。而且,到了儿童节,老师还会带大家到附近的黄金戏院看中国电影。我记得很清楚,其中一个就是《小铃铛》。
我在黄金戏院还看过不少中国电影,包括《祝福》《神笔马良》《甲午风云》《少林寺》《西安事变》《开国大典》《周恩来》《霸王别姬》等等。那个年代,看电影是件大事,父亲带我们兄妹看电影之前,还要求我们一定要先洗澡,干干净净才能去看电影。
正是因为小学的华文氛围浓,到了华中念中学时,我就负责中一的班级壁报,喜欢在壁报上写三国故事。最好笑的是历史课,老师批评说,
振义的历史测验成绩就像股市,高高低低,考中国历史就高分,考西方历史就不及格
其实原因很简单,因为我一看到巴比伦、十字军东征这些,就懒得看,更懒得背;读到中国历史,就兴致勃勃。
。我小学念华校,学的是英文第二语文。但是,上华中之后,由于华中是特选学校,华文、英文都是以第一语文水平教授。
2023年,为了纪念李光耀百岁冥诞,出版华文书《100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?》,收录
双语教育,才让我后来在职场上能够从容游走于中文、英文两个世界,也让我对自己中华文化的根有比较深层的认识和认同
可在友谊书斋、大众书局、草根书室、友联书局、Kinokuniya和卓尔书店购买。
(中新建交35周年照片展,有关于新航开通北京航线以及招收中国籍空姐的历史照片,欢迎参观。图源:新华社)
1985年,我第一次出国、第一次坐飞机。当时我们学校乐队代表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参加比赛。同年1985年5月15日,新航开通上海、北京航线,拉开了与中国内地通航的序幕。当时我就想,要是年底这场比赛是在中国,该有多好!
到了高中时期,很羡慕那些拿政府奖学金到台湾念中文系的学长学姐。到今天,新加坡政府奖学金也可以到北大清华等大陆著名高校留学,而且门类不仅中文系。可见两国关系发展之全面和高速。
。那一年,我到了台北。所见、所闻,完全就是我对中华文化的期待和仰慕。尤其喜欢台北的书店,当然,卤肉饭、焢肉饭、鹅肉、烧肉粽等等,都是回味无穷的美食。
一向附庸风雅。到了台湾看到好多刻印章的小店,来来走了几遍,实在忍受不了诱惑,忍痛掏钱刻了个牛角质地的姓名章。回到新加坡之后,满怀欣喜地把家里所有的书,在扉页上都把它盖上了。前几年,我在台湾师范大学教书,又看到了刻章的店。这次不再犹豫,给女儿刻了个章。我心想,希望孩子长大之后也能有一些中华文化气质。
当时入境台湾还有个规定,就不可以携带有任何带着“中国”的东西。所以,连带有“中国制造”四字的小锁头也不能用。当然,后来就没有这种要求了。
两年半服役之后,1990年进了大学,自然而然选了中文系。那一年10月3日,
到了1993年,中文系出现两件事,都跟中国有关系。一个是引入了好几个年轻的中国大陆老师,包括张敏、张洪明等,教育学生的方式让我们耳目一新,至今令我受益匪浅。
另一个是林徐典教授卸下系主任一职。林教授的学术成就在此不赘述,他在荣休仪式上的一番话,我记忆犹新,大意是说,中文系的同学们不用担心前途如何,因为
毕业之后,我当了几年消防官,后来,回到国大念MBA。恰恰是这个MBA,让我人生发生了变化。
在念MBA之前,我总是觉得,文人就应该清高,温饱就行,挣钱做生意这种事,文人不屑也不必碰。但,读了MBA,我才开始发现,原来经商也有其中的学问和修养。更重要的还有两个事。一个是我选修了不少跟中国有关的课,如“中国商务”“中国与WTO”,开始对现代中国商务感兴趣;另一个是我接触了不少中国留学生,对中国人的学养、见识、经历,刮目相看。从此对中国的兴趣更浓厚了,一心想到中国去发展。这时恰逢九七。6月30日午夜,守候在电视机边,看着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,不由热泪盈眶。当年念近代史,读到战争总是唏嘘。现在看着香港回归,真是百感交集。后来才知道,好几位中文系老同学都有激动澎湃的情绪。跟我一样,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。
所以,过了不久,当新加坡贸易发展局招人的时候,我毅然“投笔从戎”。很快的,在我面前掉下了两个天大的好机会。
首先,我在总部担任华南与港澳处长,后来,也开始负责山东、四川方面的工作。这些工作让我非间接接触中国官员、中国企业,学到了不少,也交到不少好朋友,尤其在山东省外经贸厅。
然后,第二个天大的机会来了。驻上海商务领事职位要轮换,局里本来物色好了人选。偏偏
2002年初,我外派上海,担任商务领事。在这个任上,我负责协助新加坡企业在长三角地区投资。
。物价也突飞猛进,我刚到上海时,请客吃饭只要不点鱼翅鲍鱼这类名贵菜,基本能不必看价格,随便点。2013年,我在北京大董请客时,一看菜单吓了一跳,除了一个凉菜,其他价格都是三位数;即便是凉菜,也只是其中一道是两位数,其他都是三位数。
两年后,2004年我下海。跟两年前同事抗拒去上海完全相反,我辞职的消息一传出,马上有好几位年轻同事毛遂自荐。尽管前后只差这么两年,
。2004年到一家上市公司的泰兴公司担任总经理;2007年到北京,担任中国新加坡商会的首任全职总监,后来担任美国跨国公司的北京大区经理;2011年担任通商中国首任总经理;2012年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事务处主任。2015年担任隆道研究院总裁等等。目前在《新加坡眼》,也是跟中国读者打交道的多。
我家四代人,祖父母先是清朝子民,然后是民国百姓,然后是民国侨民,然后是日本占领时期的牛马,然后是马来西亚公民,最后成了新加坡公民;第二代,父亲母亲也经历了侨民、沦陷牛马、马来西亚公民、新加坡公民的过程;我是第三代,一出生就是新加坡公民,但与中国关系很密切。到了我孩子这一代,跟中国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。母亲原籍中国不说,她第一次出国就是去中国台湾,那时才两岁;再大一些,几乎每年都去中国大陆,有时一年还去两三次。
而且,在幼儿园里就有中国新移民朋友,不像我,一直到20多岁念大学才开始接触中国人。
在90年代末之前,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不多。那个年代,在公共场地如果听到中国口音,肯定会转头看一眼,因为少见。而且,当时,新加坡的中餐主要都是传统粤、闽、琼、潮汕、客家菜,极少有中国别的地方的菜馆,百胜楼的天津馆是一家。
现在呢?中国新移民、中国客工、学者学生、教师、护士、巴士车长,到处都是。中国菜更不必说,川菜、湘菜、河南菜、江浙菜、新疆菜、东北菜等等,几乎什么都有。中国式烧烤更是满大街都是。以前新加坡不怎么喝中国白酒,现在喝白酒的慢慢的变多,比如汾酒、茅台。
不仅传统行业,就连前沿的中国机器人,也走进了新加坡。新加坡副总理到深圳时,也打卡了“中国智造”。
现在中国已进入到新加坡的方方面面。同样的,新加坡也进入中国的方方面面。自2007年以来,中国是新加坡的首要投资目的地。到了2013年,新加坡成为中国的最大投资者,这个记录从始至终保持到今天。
前不久,新加坡外长维文说,新加坡独立以来取得的发展,归功于一些因素,其中一个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。
,hth网站